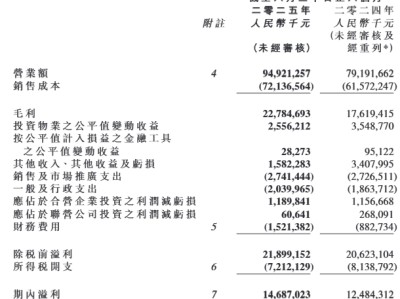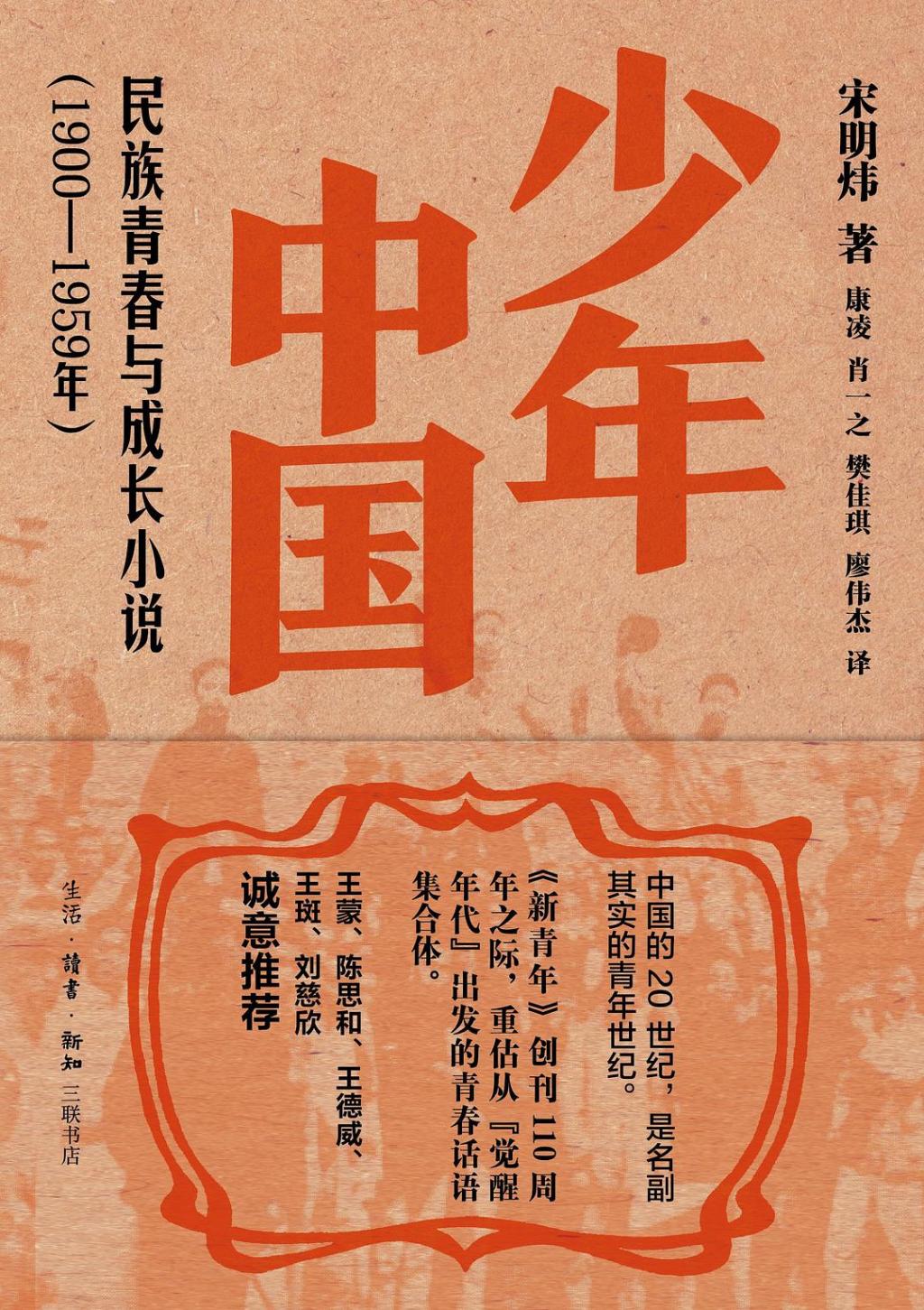
《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宋明炜著,康凌、肖一之、樊佳琪、廖伟杰译,2025年5月出版,366页,60.00元
“新中国”的概念,作为一种“未来”想象,诞生在二十世纪之初。二十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认同的第一个“世纪”,时间本身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而中国的历史有了未来指向。新旧世纪之交,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青年领袖梁启超(1873-1929),恰巧在横渡太平洋的中途感悟世纪更迭的意义:“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即将开启的新世纪预示着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非凡前景,而梁启超以诗意渲染的时空体并非实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旧邦,而是想象之中居于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版图的新世纪的未来中国。尽管晚清最后十年开启的时刻,二十世纪伊始,正值变法失败、庚子国难,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空前绝望的时代,但也是在这十年中,孕育了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学的乌托邦传统。在梁启超及其同志的笔下,各种乐观的政治预言、未来时态的小说叙述造就了想象的“新中国”。
在中国经历的第一个世纪初,梁启超将未来中国定义为一个充满新生活力的“少年”国家,称“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而他想象的少年中国,借鉴他仰慕的“少年意大利”,是一个渐趋“完全成立”的现代主权国家。与此同时,梁启超撰述《新民说》,从进取精神、权利思想、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进步、合群、尚武、政治能力等多个方面,勾勒出有“独立之精神”的理想国民形象。这种种政治论述,最终进入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以革新文学来启蒙民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并且亲力亲为写作政治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然此作未完,却成为新小说的经典,为同时代作家表达政治诉求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述结构及目的论的情节模型。
晚清小说既有揭露社会无边黑暗面的“谴责小说”,也有种种想象华丽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首先预设六十年后的中国,已然是一个世界强国,而此强国并非完全抄袭西方列强形态,而是以儒教复兴获得道德上的理想型形态;改良派小说家吴趼人,则在《新石头记》中从二十世纪初的政治泥潭一跃进入充满未来色彩的“文明境界”,这一个看似模仿凡尔纳科幻奇景的世界,却处处强调其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政治制度,以及从中国固有知识传统演变出来的各种发达科技 ;此外,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反写十九世纪种族论述,描绘中国出征欧洲,大败白种民族 ,陆士鄂《新中国》畅想立宪四十年后的中国雄冠世界,万国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而浦东陆家嘴已然是国际金融中心 。这些结合政治狂想与科学小说的作品,在晚清有将近十年的繁荣期,其中孕育的乌托邦冲动,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充盈中国的政治文化空间,以民族自新为基础的“新中国”论述继续发扬,持久不衰。
今天距离梁启超发明“少年中国”,提倡“新小说”,启发一代作家书写新中国主题的未来小说,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梁启超在小说中试图演绎的六十年未来历史,那个“未来”的时刻表已经走完了两轮。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少年中国》(Young China),后来经过修改在哈佛大学出版,这个论述的构架和完成也已经有二十年了。中文版近日由三联书店推出,我自己检视一遍,却颇有一种失落感。自己早已不是当年在图书馆里昼夜写作不停的青年,而我在书中论述的“少年中国”及其种种表象在当前的语境中都变成过时的大说。
《少年中国》究竟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延续着现代性主题的论述与辩证,其中最突出的象征意义是赋予历史时间一个目的论的形式。“少年中国”和“新青年”论说的基础是预设未来的乌托邦愿景。其中交织着现代性的诸种意识与意识形态:社会永久的进化、进步;国家如一个青年那样的不可逆的成长过程;文学则也是这样一个不可回流的时间长河中的浮标。《少年中国》着重研究的还是青春话语在文学中的形构过程,这就是现代成长小说的诞生。后者是以单一主人公为叙述主体的现代小说形式,这是近代小说最凝练、最经典的叙述形式,中国青年们走过的一段段人生旅途——倪焕之、梅行素、高觉慧、蒋纯祖、林道静,构造了目的论小说叙事的结构与形态,但同时如是的现代小说也表达了现代性在民族国家层面的精神追求。
原著之所以从1900年开始,结束在1959年,当然从梁启超提出《少年中国说》到新中国十年献礼电影《青春之歌》上映,这恰是一个甲子,从话语到意识形态,从论述到小说叙述,都完成了一个趋于经典化的论述。但在此之后,此一奠基在现代性论述基础上的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在中国文学中逐渐褪色、隐匿。不是说此后就没有了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但现代性的时间、国族、结构上高度统一的表述和文本却在此后的又一个甲子(1960-2020)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甚至到了1980-2000年间,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反对、超越成为时代的一个新主题。虽然也许并不缺少新青年,但成为时代象征的却是另外的青年形象——顽主、白领、消费主义者。“青春”成为可以消费的对象、可以浪费的能量,但另一方面“青春”不再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新一代永远年轻,似乎再也不会老去了。
我在完成《少年中国》的时候,开始关注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在梁启超畅想“新中国未来”、开启了政治理想小说和科学小说的乌托邦叙事传统的一百年后,中国文坛再次出现了融合政治想象与科幻小说的写作。新一代作家对中国主题做出各自的回应,无论是光年尺度上雄浑崇高的“光荣中华”,还是地下世界幽暗深邃的“鬼魅中国” ,都在构想不拘一格的“新中国未来”。我称之为科幻新浪潮的一种具有先锋意识的写作,犹如少年中国倒影里释放出的梦魇,打开现实中不被“看见”的方面,在技术和想象层面打破了现代性的确定与目的论,反而指向测不准的未来。在科幻小说中,无论是《三体》中的黑暗森林,还是《地铁》中的未知世界,所有此前我们用以解释现代性的知识、话语和思维定式,都不再有效,如我在此前论述中所说:“表达不可能与不确定的世界,在科学和政治层面想象未来的历史,超越已知的、可见的空间,这些特征已经使得科幻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它犀利地切入那些(即使是微弱地)意识到有别种可能性的大众想象与知识思考。”
但我也认为新浪潮对于文学想象主流模式的颠覆意义,不仅局限于科幻这个文类,也以“科幻性”(science fictionality) 的影响在重塑更广义的二十一世纪华语文学。所谓“科幻性”表征文学对于传统写实模式的不满,放大了文学想象在未知和不确定层面具有的启示力量, 在科学技术加速重塑世界的呈现方式与人们的感觉结构的情境中,指向超越既有政治和文学范式的可能性。自觉将“科幻性”引入文本实验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多,如科幻新浪潮那样,打开了不同于二十世纪(梁启超的世纪)的新面向,而更具有“新”小说的文本实验自觉。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回头看二十世纪的新中国想象,不仅强调出小说叙事的历史后设意义,而且也往往写出乌托邦漫长暗影、从机制中发现算法的全面管控、在新民或旧民中看到后人类身影。 过去十五年,我自己未曾预知,由对新浪潮科幻以及呈现“科幻性”的中国小说的分析,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地形图中让我用另一种方式重访“少年中国”,只是此处科幻想象的未来中国,与梁启超辈们心中的少年中国,已经迥然有异。充满危机意识和末日意识的科幻小说中,现代性目的论轰然倒塌。当代科幻作家和借用科幻性来写作的作家,要克服“看的恐惧”,敢于发现别人想不到的“真相”,但在文学的基础上,他们所遵从的小说伦理,也正是对梁启超在一百二十年前提出的新小说主张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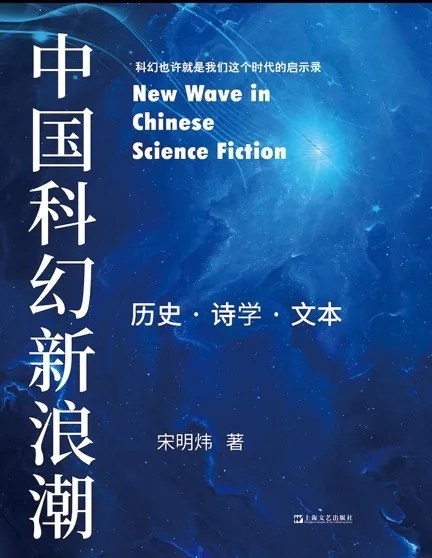
《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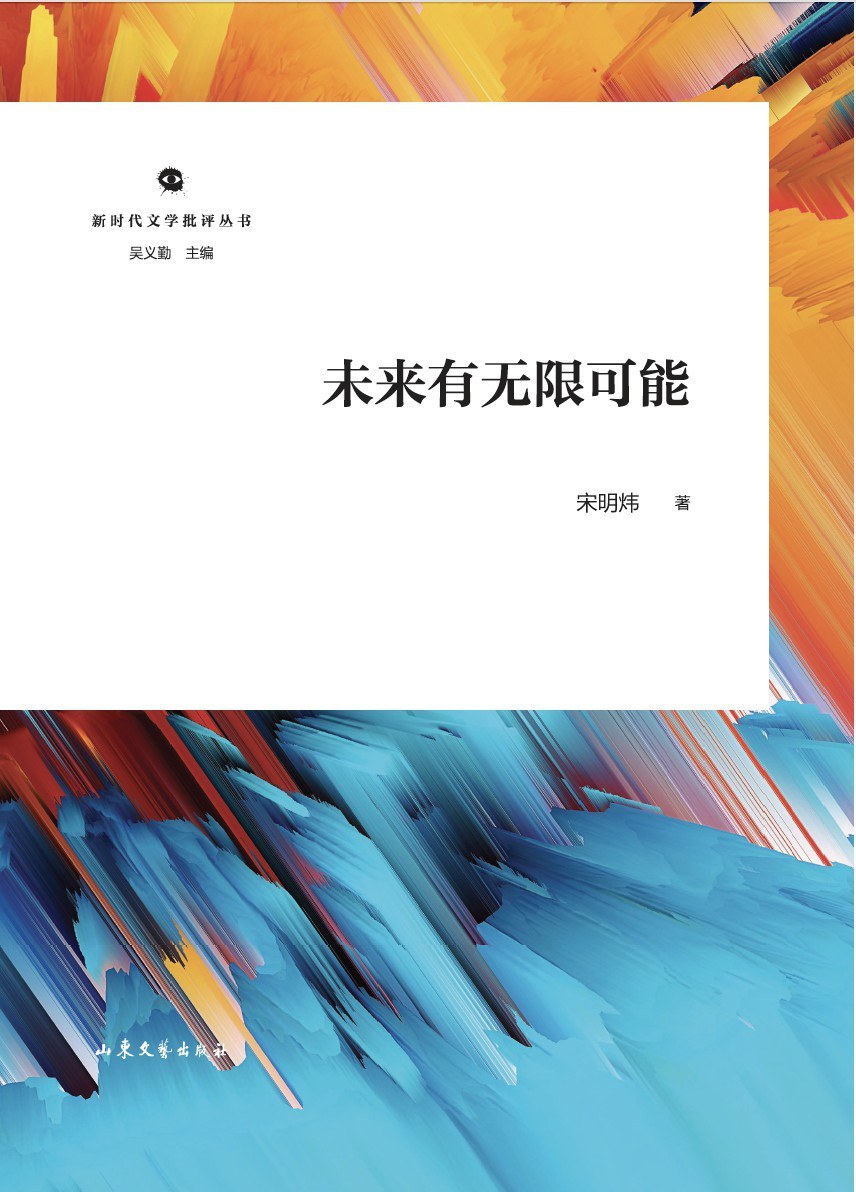
《未来有无限可能》,山东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最近回应年轻朋友的题目,我将现代性的少年中国理想比作一头巨兽,《少年中国》所要处理的是现代性这个超级知识-感知结构的发生与嬗变。这个结构在过去两百年主导世界,但也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逐渐式微。它的结束,标志着我们时代一种新的“当代”感受的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具身性和个体位置,而所有在微观层面的 “微小抵抗”或“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实在”,针对宏大理想虚空承诺的“逃逸”,而非蒋纯祖式的理想耗尽。过去,从梁启超到杨沫,都在试图建构一个尚未存在的新世界。今天我们已承载了太多现代历史文化的重负,它变得巨兽化、怪物化。科幻小说透过克服看的恐惧,去写词与物之间的深渊,我使用了“打孔”(perforate)和“穿透”(pierce)的比喻:我们杀不死现代性这头巨兽,但可以在它身上穿孔。这样说并不就是反叛少年中国理想,而是当这个理想从梦想的种子变成充塞时空、无处不在的巨兽时,我们在各自位置上能做的事——一种更微观的抵抗和穿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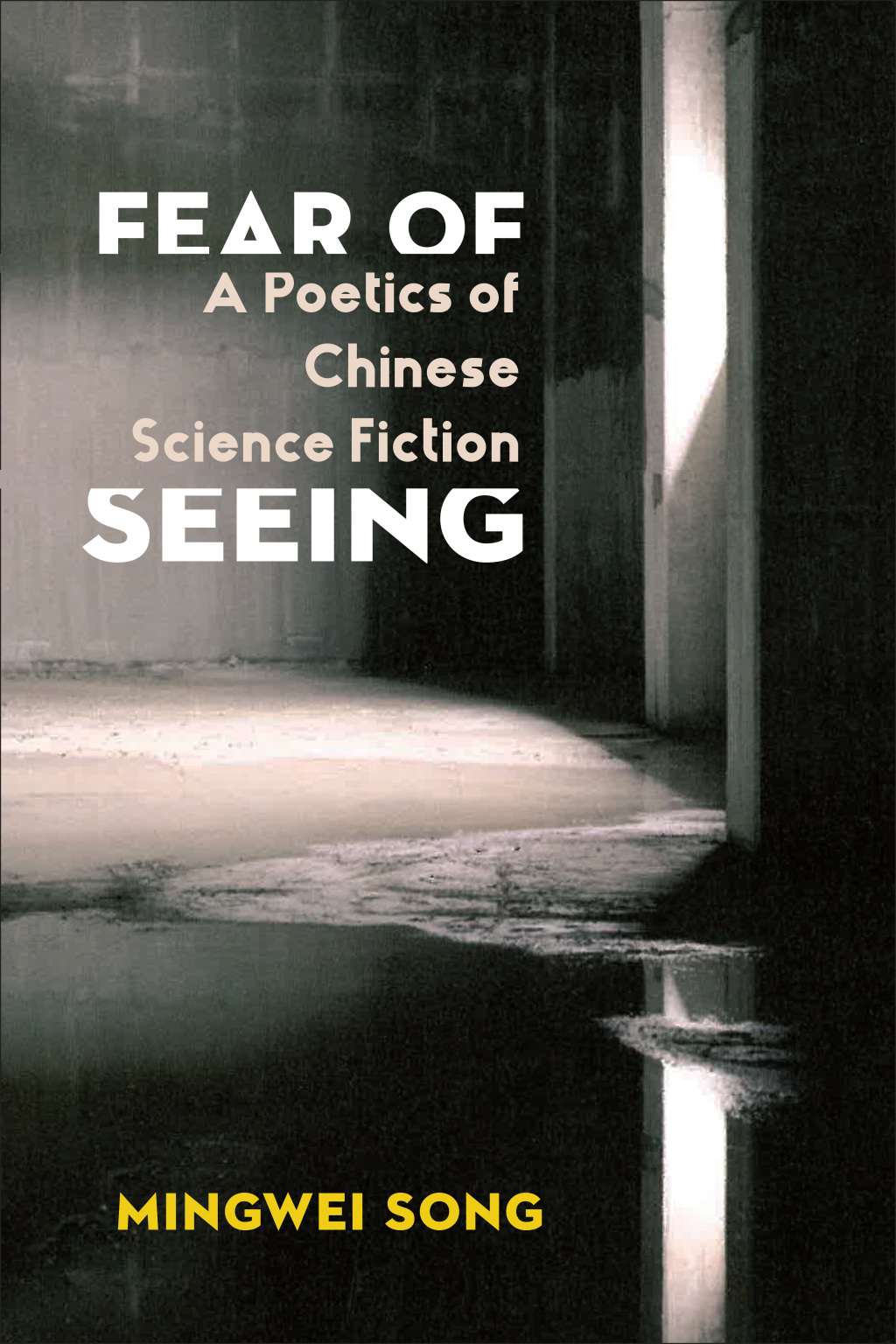
《看的恐惧》( Fear of Seeing),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